全站通知:
傅融-约会/繁云火浣
刷
历
编
阅读
2025-02-07更新
最新编辑:丧心病狂幽幽子
阅读:
更新日期:2025-02-07
最新编辑:丧心病狂幽幽子
< 傅融-约会
跳到导航
跳到搜索
繁云火浣·壹
书房
◆傅融
门窗都合上了,呼,等我把灯笼剪亮些。
◆傅融
去年新岁拜见之后,半个时辰就把见礼清点完了,今年多了许多,我看看……
◆傅融
除了没法入室清点的马匹、牛羊之外,今年一共是大礼箱五百一十口,礼二百二十口,礼匣七百六十口……
◆傅融
啊……
◆傅融
收一收收一收,别像眼里没见过大钱似的……这口箱子,接着开这口箱子……
◆傅融
啊……
◆傅融
这口这口,再开这口……
一个时辰后
◆傅融
眼睛被闪花了……等我歇一下,起来记档入库。
◆傅融
……别搞这些,不行。
◆傅融
你喝醉了吗?这种留把柄的事……蒯越才会干吧。
◆傅融
爱财如命,也要取之有道吧。
◆傅融
我推开一口半开的金器箱子,在地上躺了下来。他半侧着身坐在旁边,低头勾着礼单。
◆傅融
……
◆傅融
……没有,就是年终事繁。
◆傅融
想到见礼多了,入库的人手也多了。过手的人、记档的人、看管的人、盘库的人……
◆傅融
从前都是几个自己人一手办了,从没焦虑过可有中饱私囊之事。往后,就不一样了。
◆傅融
……
◆傅融
记档呢……
我坐起来侧身,吹灭了他手边的灯火。
片刻后,身侧的黑暗中响起一声叹息。随着衣物摩挲声,他缓缓躺在了我身边。
◆傅融
……外面在敲夜钟呢,亥时了。
◆傅融
外院还是很吵,从前,亥时差不多就静了。
◆傅融
你以前不用镇日花时间应酬这么多人事的。
◆傅融
那年,就几个自己人,在简单的晨起拜见后,下午就在内院里烧染炉吃。
◆傅融
陈登带了鱼,徐庶带了酒,阿蝉带了羊肉……其他人都带了些菜蔬点心,从下午一直闹到入夜。
◆傅融
入夜了,北院各所的仆人、侍从带孩子来领过粮米酱酒、布匹丝线和压胜钱,再看夜市放了烟火,一年也就过了。
◆傅融
那时候没想过,后来会有那么多人。光是新岁晨昏拜见,就要从卯时拜见到申时。礼毕还有夜宴,还有入幕私谈……
◆傅融
尖叫什么……
◆傅融
……
他没有笑,也没有怒,静静地躺在那,一言不发。
我伸手拂过他额发,触及某物,指尖微微蜷起。
繁云火浣·贰
书房
◆傅融
……
◆傅融
……没事,夜宴上多喝了几杯,有些酒气,眼睛湿漉漉的。
我坐起身,将他挪到膝头躺下,梳理他被泪水染湿的鬓发。
◆傅融
……别闹,这是书房,被人看见……
他想起身,被我摁了回去。纸窗外夜光幽静,我望进那双眼眸里,没有说话。
那些原本试图躲闪迂回的话也一同被止住,眸光流转新岁的薄月,无处可藏。
◆傅融
我新年……不打算回家。想留在广陵。
◆傅融
……嗯。能不回去吗?报我留守值班。
他终于笑了,微微侧过身,就着这个姿势,蜷缩着紧紧拥住了我。
◆傅融
……我不想去别的地方。不想去陌生的地方。你去江都吧。
那双眼睛微微抬起看向我,旋即又垂下眼眸,双手紧了紧,摩挲过我的腰际。
◆傅融
这么做,好像是我在扫兴一样。
◆傅融
……不可惜吗?
我拉过一口旁边的礼箱,那礼箱比其他礼箱更轻些,里面似是织物之类。
从箱子里取出的,是一件鼠背灰的披风。款式简单素净,并无出奇之处。
他摸索着点起灯火,初燃的火星落在了上面,织物上燃起火苗,但旋即熄灭,被火烧过的地方渐渐洁白,如同被火焰洗净。
◆傅融
火浣布不是那个周穆王的传说吗?
◆傅融
一寸百金……我们去昆仑山织布吧……
◆傅融
织两年就能买下全广陵的房子……一间给飞云,一间给绣球,一间给金子……
◆傅融
你笑什么?
◆傅融
那还卖那么贵……穿着也不舒服,比寻常布料重很多……
◆傅融
旁边这口是丝绸……这口里面还是金器。金器,金器,丝绸,金器,香料,金器……
他将礼箱一口口打开,起初还有些惊喜,直到金器如石子般堆了满地,便也觉百无聊赖。
◆傅融
不能直接倒出来!金子很软,万一压变形了……唔啊!
◆傅融
不能倒!万一有什么紧要的见礼被摔坏了,以后要落人口实的……不行!
◆傅融
红珊瑚树啊——!!!
他拿起断枝试着拼回去,绝望地叹了口气。我大笑着把他拉回来,拉到下一口箱子边。
◆傅融
不……要……啊……
◆傅融
啊啊,玉器都捧碎了……哈……你……哈哈……是夜宴也喝多了,玩上头了吗?
那双眼眸稍明亮了些许,含半抹醉意看我。松散的发冠不知落在了何处,长发映着纸窗外的雪月光,散着素净好看的光。
他也推翻了一口箱子。烂漫璀璨的金器宝石光倾泻而出,若东海雪沫碎光,溢了满地。
我们躺在那块火浣布上,身下便是倾国倾城的金器堆。灯火灭了,但室内很明亮,无数金银珠宝映出夜光来,照亮了他呼吸的起伏。
◆傅融
真是浪费......金器下面,肯定压碎了很多宝石。金器也都变形了,不知道能不能修……
◆傅融
哪里有意思,简直无药可救。
◆傅融
我也没得救。
我翻身伏在他身上,他先是侧头移开目光,但被我的手指搭住脸颊,转了回来。
◆傅融
……唔……唔……
◆傅融
唔……
◆傅融
被什么硌到了……好像是那颗珊瑚树……
他动了动。声响被身下金器散落的声音掩盖了。我感到他的手在寻找我的手指,轻轻扣住。
随着动作,金器将将滚落。垫在身下的布料并不透水,身躯被微冷的潮感纠缠着,像眠在春日东海的浅浪灰沙之上。
◆傅融
我有些渴了。这个好像是……酒壶吧。
轻响中,他从一旁堆砌杂乱的器具中摸出了一支玉酒壶,随意打开封口,清冽的酒香就涌了出来。
◆傅融
……寻常的节礼酒,不好喝。
我用脚踝抵了抵他,被他按住膝盖。他的手心发烫隔着纠缠在身上的单衣依然能感觉到热意。
他俯下身,借双唇渡给我一口酒。这个吻绵延许久,直到彼此都微微眩晕,方才给对方留出生路。
◆傅融
……嗯……
◆傅融
……哈……就一口,你就喝醉了吗?
◆傅融
那……你还要酒吗?
◆傅融
喝醉的话……会被抬到祭台上去的……会这样……一点一点的……
温热的唇,在身上留下或浓或淡的酒痕。酒意是微凉的,让人不自觉地去寻着人的温度。
我忽然动了动。他握住我的手,又像被烫到般松开,却被我紧紧扣住十指。
吻过的唇瓣在思考之前重新追逐彼此,齿问仿佛含着一团湿润的火焰,渡来更多的酒液。
◆傅融
又不是没见过山崩地裂……唔……放松一些……唔……
他落下更重的吻。金器摇落,若山峦惊飞鸟。春水柔润穿过山涧,浸染生发出无数或深或浅的山鸣。
繁云火浣·叁
书房
房间还没有烧暖,身躯在寻求彼此的温度,几乎淹没所有的空隙。
他顺着我的动作前倾,长发如网般笼住我,与肌肤的触感相纠缠。被酒液濡湿的额发贴在眼角,若未干的、潮涌般的情泪。
◆傅融
你是……神使巫女吗?
◆傅融
能让我去更深处……问天意吗……
长发发梢扫过我颈上,像藏蓝花叶堆砌在颈上胸前,留下一丝丝的痒意。
痒意随着他的舌尖流连到别处,我拉过他的手腕,吻在手腕脉搏处。
◆傅融
……离得太远了,还是……听不清天意……
◆傅融
再近一点吧……稍微放松些……再近一点……
金山隆隆而崩。仿佛旷野下交错的缠枝根系,在甘泉下深深没入,索求汲取。
火浣布上有两尾求水池鱼,相濡以沫于梁下夜影之中,身周云水雾气,丝丝钻入骨头缝隙里,往更深处催问着回响。
◆傅融
这样……会更清楚吗?
他抱紧了我,就这样坐起了身。春水涌入更深处,几乎触及深涧尽头,回溯涌流。山风声掠过耳畔,在眼前惊起无边银白潮浪。
◆我
……还没结束……
潮浪奔涌,倾泻蒸腾进无孔不入的朱栾香中。夜色更深。
火浣布已经皱褶得看不出原型,反复揉皱下沁浸的水色深深印入身下金山。在最后一阵的激荡中,金山訇然塌散……
书房
我们依偎着睡去,月已上中天,雪夜静静的,透过窗子,郁郁雪松摇影,像天上落下的扇。
◆傅融
篝火?不是已经结束了吗……晚宴的时候就烧过了,花了府里半个月的柴火。
◆傅融
人太多了……说眼前的事,这个……这个怎么办……
他揉了揉那团火浣布。
◆傅融
这个就丢了吗?……毕竟是这么贵的布料……直接丢了,好像有点……
◆傅融
交给别人清理也……要不,我悄悄去洗……
◆傅融
……
◆傅融
那我去洗了。
◆我
天尊。
他抱着它,惴惴出去了。我叹了口气,躺回金器堆里。
◆我
……该不会真的去洗了吧?
广陵王府
我随意披起外衣,步过渡廊。他没有走远,在院角的水井边坐着。
◆傅融
……
◆傅融
……
他侧过身,半背对着我。我走过去,手掌轻抚在他背脊上。
◆傅融
……要不要走?
◆傅融
去江都。
◆傅融
今夜。
他抬起头,怔怔望着我。接触到那眼神的霎那,心里似有一根旧弦,被无声弹拨了一下。
◆傅融
……今夜就去。我们一起去。
◆傅融
我们骑马去……不用带什么,就我们俩,别让别人跟去……
◆傅融
去吧!一起去!
他丢开了那团价值连城的布,不顾肩上披的外衣滑落雪地,起身拉住了我的手。
◆傅融
就今夜,两个人一起走。
◆傅融
……我给你带来过夜光螺的,你记得吗?
◆傅融
我不要别的……那些什么……哈……什么三千万的纸条、什么官至三公的空口白话……天上地下,我只要这个,行吗?
城郊
◆傅融
……
◆傅融
……先去,去到哪算哪。
我们策马夜奔,跑过城外茫茫白雪。新岁夜深,城内外夜市都已经停了。白雪上留下爆竹狼藉,像随我们夜奔的鬼神足迹。
我赶上了他,拽住了他的坐骑缰绳。他的马被勒住了,散乱的长发在雪风中飘荡,弥于眼眸之前。
我们沿着雪道,赶往界碑。风雪漫天,他的披风不知何时松脱了,但人浑不在意,只策马向前。
◆傅融
……它跑不动了吗……
◆傅融
……不用,我没事。
他回头对我笑了笑,忽然想起什么,仓促勒住马。
◆傅融
飞云……我们忘记带飞云了……
◆傅融
……不是的,不是的……
他拉动缰绳,试图让马匹调头。但坐骑的马蹄卡在雪石之中,一时难以抽身。
◆傅融
我把飞云丢下了……我怎么会把它忘了……你在这等我,我回去接飞云!
他翻身下马,步行跋涉过无尽的雪天,回头朝着城影方向折返。我牵动缰绳转向,试图拦住他。
雪风中,傅融抬头回望我,碎雪染白眉眼鬓发,像褪了色的影子。
又有一道马蹄声从雪道另一头由远及近,是一名披着褐色雪披的儒生。见我们俩停在道中,他本欲勒马绕道,但见到我们,此人又犹豫了起来,似是相识。
他一意往回走,我也只能策马跟上;那儒生匆匆跟来,喊住了我们。
傅融的脚步停下了,缓缓转过身,目光落在对方身上。那青年拜礼完毕,拂衣起身揖了揖,告退上马。
◆傅融
……夜深了,我们回去吧。
◆傅融
你说得对,今夜雪太大了……后天再去吧,后天,众人一起去……
雪声呼啸,他迈过齐膝深的积雪,走回了坐骑边。马已经挣脱了雪石,立在道边,静静等着他。
数日后
江都别院
几个侍从聚在纸门前,争论着梅花消塞图的事。我和傅融坐在廊下,看着今日附近送来的手帖。
◆傅融
今年雪其实积得挺好的,早上附近都有雾凇了。我起得早,清晨带飞云出去时候看见的。
◆傅融
天没亮就听见檐下有冰碴落下来的声音,滴滴答答的,人就睡不着。
◆傅融
我想你醒了还要传漱洗和早膳,我吃早膳不喜欢坐在那等传膳,就从后院取了点饵饼,随便吃了点,带飞云出去玩了。
纸门前的人散去了。身后静了下来。我回过头,见纸门上的消寒图已经点得密密麻麻。
◆傅融
说了要点九九八十一天的,结果每年都是头两天就忍不住点满。
他挪坐过去,点起了小孩子们刚才乱点的梅花。
◆傅融
七十二、七十三……点了七十五朵,还留了一些每天点吗?
门前还有几盏未干的朱砂。他拿手指着,在空白处点了几下。
◆傅融
七十七、七十八……不能点多了,不然开春就晚了。八十……八十……啊!飞云!
飞云踩过了一盏朱砂,好奇地扑上纸门,门上立刻多了一堆梅花。
◆傅融
看看还能不能补救……把那团红的改画成红衣小人?不不不更恐怖了……那画成红色的落花……
◆傅融
咳咳咳,可以的,应该可以改成功的,我再想想……
片刻后
◆傅融
……
◆傅融
多可爱啊你看,给……给它穿个红棉袄……
◆傅融
实在不行重新画一张吧……不要哭了,不要哭了啊……
江都别院赏月的第二日,从一幅穿着红棉袄的消寒图,和侍童们此起彼伏的哭声开始……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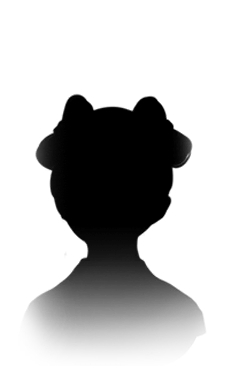



 沪公网安备 31011002002714 号
沪公网安备 31011002002714 号